柯杨:民间歌手的才能——兼论洮岷花儿对唱中的环境因素
2017-05-18 | 学术争鸣 | 阅读量: | 收藏此文
摘要: 原文发表于《民俗研究》2001年第2期 在中国甘肃省东南部洮河流域的临潭、卓尼、岷县、康乐、临洮等县的汉、藏、回三个民族中,长期流传着一种被称为洮岷花儿的山歌。当地农民除了平常田间劳作、山坡放牧时偶尔即兴歌唱外,还在传统的、一年一度的花儿会上,自发地举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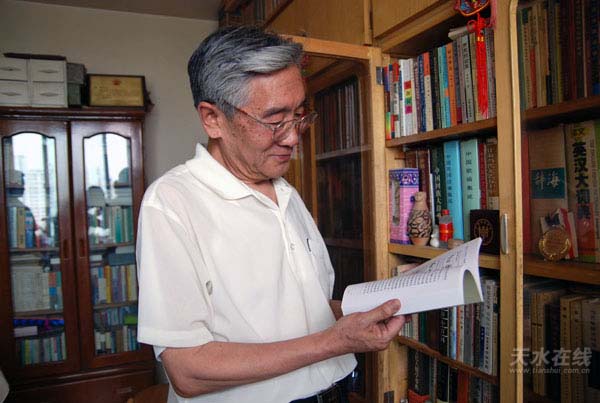
原文发表于《民俗研究》2001年第2期
在中国甘肃省东南部洮河流域的临潭、卓尼、岷县、康乐、临洮等县的汉、藏、回三个民族中,长期流传着一种被称为“洮岷花儿”的山歌。当地农民除了平常田间劳作、山坡放牧时偶尔即兴歌唱外,还在传统的、一年一度的“花儿会”上,自发地举行大规模的山歌竞唱活动。岷县二郎山花儿会(农历5月16日—18日)、临潭县新城乡城隍庙花儿会(农历5月4日—6日,端午节)和康乐县莲花山花儿会(农历6月1日—6日)的规模最大。
最初,唱花儿是农业祭祀仪式的一部分,是人与神交往的一种重要方式。这从我们搜集到的“神花儿”(即专门唱给神的花儿)中可以看出端倪。其内容,或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或祈求生儿育女,繁衍子孙;或表达愿望,求神佑助;或因愿望得到实现而用歌唱酬谢神灵。后来,艺术从祭祀活动中分化出来,向娱乐转化。从洮岷花儿中情歌、生活歌的逐步增多,祀神花儿逐步减少。
在洮岷一带的花儿会上,民间诗人、歌手们的即兴创作和演唱,总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包括: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演唱程式(包括禁忌)的制约;对唱者相互问答的激发作用;现场听众的反应和参与程度;赞助者对歌手的奖励和权威者的态度等等。这诸多因素的综合,往往支配着歌手们的情绪,也对演唱的质量和效果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一、花儿会上传统的演唱程式与禁忌
花儿会,可说是洮河流城民间诗与歌的盛大节日。农民们的演唱活动,数百年来。形成了一定的程式,当地人叫做“规程”。
比如莲花山花儿会,每年总是按下列顺序移动进行:农历六月初一、初二两天,以朝山进香,祀神酬神和唱“神花儿”为主。初三、初四的白天和晚上,歌手们聚集在莲花山下的足古川里,大唱生活歌和情歌。初五移到景古乡的王家沟门彻夜对唱。初六,一部分移到临洮县潘家集的紫松山,另一部分移到临潭县冶力关乡的关街,除继续唱情歌、生活歌外,还必定要唱告别歌,表示一年一度的莲花山花儿会即将结束,相约明年再来聚会。至于莲花山附近各村庄青少年们在花儿会期间用马莲绳拦路听歌的风俗,也是最有地方特色的“规程”之一。
再如临潭县新城乡端午节的花儿会,是从明、清以来的迎神赛会演变来的,共举行三天。第一天叫“跑佛爷”,各乡村的青壮年天一亮就用轿子抬着他们的地方保护神——龙神(共有十八位)来到新城外,先举行“献羊”仪式,下午集中到东门内,经地方官员和商会会长等主持“降香仪式”后,人们便抬着自己的“龙神”飞跑,以最先到达城隍庙大殿落座为胜。第二天叫“踩街”,各此赛神队伍抬神轿、举銮驾、列仪仗、奏鼓乐,按座次先后出城隍庙缓缓游街,两侧住户、商店皆燃炮、焚香、迎神、谢神,然后返会城隍庙重新入座。第三天叫“上山”,天拂晓时,各路队伍抬“龙神”到城西北面的朵山(又叫“大石山”)禳雹除灾,祈求丰收。中午陆续下山,在西门外岔路口“扭佛爷”。下午返回城隍庙,黄昏时出庙,各路队伍抬“龙神”回到各自本庙。在这三天当中,各地民间歌手也都跟随赛神活动移动竞唱,晚上更加热闹,城隍庙内外整夜歌声不断。
岷县的花儿会大致与临潭新城花儿会类似,只是赛神、唱歌的地点在城附近的二郎山及山下的街道上而已。至于其它规模较小的花儿会,虽然没有赛神活动,但在附近庙宇进香祀神和对唱花儿,则是共同性的。从上述情形可以看出,洮河流域花儿会的演唱程式,总是与当地的农业祭祀活动紧紧相连。歌唱时的独特声调、韵律和节奏,与日常生活中的口语大不相同,能制造出一种异乎寻常的神秘气氛,以利于人和神的沟通与交流。
每当两组歌手正式对唱时,也有一些约定俗成的规矩必须遵守。
首先,不能在家中或村子里唱情歌,只能唱“神花儿”、“本子花儿”或“贺喜花儿”。
其次,即使在花儿会上,也有“避班辈”(当地俗称“避躲”)的风俗,就是同一血缘家族中不同辈份的男女之间,不但不能对唱情歌,也不允许在圈内听歌,以免乱伦之嫌。有的歌手一开唱,先唱“有避躲的往后站,没避躲的往里钻”,正是这一风俗的反映。
第三,在花儿会上若与不相识的歌手对歌,一般都要先唱见面歌以示礼貌。见面歌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问候。比如
甲组问:“红心柳,一张杈,各位朋友来了吗?先问你们一句话,走乏了吗没走乏?”
乙组答:“一年一回莲花儿,娃娃不引门不关,痛痛快快唱几天,把兀(那)乏的再没管。”
二是询问对方姓名和家住何处。比如
甲组问:“清水倒者缸里呢,你是城里的嘛乡里的?你是阿个庄里的?”
乙组答:“针插子上一根针,我是太平寨的杨家人,白松门扇双大门。”
三是问对方想唱什么内容的歌。比如
甲组问:“杆一根,两根杆,唱个啥是你喜欢?爱石榴吗爱牡丹?”
乙组答:“园里要种白菜哩,各位把式都在哩,要唱个你疼我爱哩。”(即希望对唱情歌)
几段见面歌唱毕,就转人正规的对唱。一般说来,一场正规的对唱,大约需要三、四个小时,唱到饿了、累了,便互唱几首告别歌,表示这场对歌即将结束。比如:
“木板要做案板哩,各奔各的店站哩,肠子要连面灌哩,是牛马者安圈哩。”
“手拿镰刀割柳哩,尕怜儿起身就走哩,心疼者阿们(怎么)丢手哩。”
“海纳捂了红指甲,你去时把你的魂丢(留)下,我把魂压者席底下,晚夕连你的魂说话。”
都是生动有趣的告别歌的实例。
二、对唱者相互之间的问答和激发作用
洮河流域花儿会上的对唱,不是个人对个人,而是集体对集体。因此,双方都把对方视为最重要的听众。一个演唱小组,必然是在一位“花儿把式”(又叫“串把式”或“花儿行家”)的率领下,由五、六人组成。“花儿把式”这个重要角色,总是由那些具有丰富创作和对唱经验的歌手担任,他的主要任务,是应付对方的挑战,在极短的时间内编好歌词,并把这首歌词及时口述给自己小组内的各位歌手,由大家一人一句地轮流去唱。“花儿把式”是一个演唱小组的灵魂和主心骨,这个小组赛歌的成败,主要取决于他这个核心人物的应变能力和创作质量。有一次,我在莲花山花儿会上听到两组歌手相互赞扬对方的水平高,唱得好,他们的唱词是:
甲组:镰刀割了胡麻了,
寻着花儿的娘家了,
把花儿有处搁架了,(搁架:放置)
不由人者服下了。(服下了:佩服得很)
乙组:镰刀割了碎花了,
寻着花儿的外家了,(外家:外婆家)
唱花儿有人对答了,
有你就有配搭了。
甲组:竹子叶叶儿倒挂了,
遇上花儿的好家了,
把我听者笑下了,
心里一呱记下了。(一呱:全部)
乙组:镰刀割了胡麻了,
碰上花儿的行家了,
把唱不好的不怕了,
越唱精神越大了。
现场听众对这一段精彩的对唱,无不报以热烈的掌声。“花儿把式”们创作一首花儿,绝对不会超过一分钟,他在听到对方合唱“花儿哟,两叶儿呀”这个尾句的时候,就要给本组的“头腔歌手”(即唱第一句的歌手)口授自己心中已经编好的首句歌词,对方声落,我方声起,中间不得有丝毫停歇或冷场出现。
最值得注意的是对唱过程中双方“花儿把式”之间的相互激发作用。有一次,我在花儿会上采风时,为了记录得快一些,便约请了几位“花儿把式”在休息的间歇中把他们心中所编的歌词说出来,而不是唱出来。他们说了十几首之后,就再也说不出来了。我问他们:“为什么在对唱中你们的歌词编得那么多、那么好,而离开对唱却没有词儿了呢?”他们说:“要针对对方的问答才有话说,没有对手,就不知该唱什么了。”由此可见,对手的提问和回答,是“花儿把式”们产生创作欲望的“酵母”,是激发他们灵感与智慧的关键。没有对歌的热烈氛围和竞技环境,失去了挑战者“火力”的逼迫,他们即兴创作的才能就难以充分发挥出来。
双方“花儿把式”的相互激发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有问必答,不能答非所问之外,还包括对对方声音太小或突然停顿的洁难和嘲笑。当地所流传的“花儿好唱,把式难当”这句俗语,强调指出了“花儿把式”在对唱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那些优秀的“花儿把式”面对激烈的竞技场面,沉着冷静,从容不迫,他们一边喝着浓茶、摇着扇子,一边编着唱词,指挥着本小组的歌唱,一派大将风度,不能不使人们佩服得五体投地。
三、听众与歌唱者之间的感情交流
不参与歌唱的听众,有的是专程前来为本村歌手助威的歌迷,有的是朝山进香的善男信女,有的是远道而来的观光游客,有的是从事民间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这些听众与歌唱者之间,也有着明显的感情交流,对歌唱的内容与气氛的热烈程度,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本村的邻居熟人中,以替补歌手、歌迷或“花儿把式”的崇拜者居多数。他们虽未直接参加演唱,只是坐在内圈听歌,但却是本乡本村歌唱小组的坚定支持者。他们不时为己方精彩的演唱大笑、叫好,甚至提出建议,起一种智囊团的作用。
比如,1988年我在莲花山花儿会上采风,一个小组唱道:“莲花越开越艳哩,包产到户实现哩,农民生活改善哩,顿顿要吃白面哩。”本来,唱完这四句,就该唱“花儿哟,两叶儿呀”这个尾句了,但内圈的一位歌迷觉得这几句把生活的改善表达得很不充分,居然灵机一动,越俎代庖,补作了三句,让歌手们接着唱:“长饭还连油拌哩,里头和点新蒜哩,香者只把嘴伴哩。”而另一位歌手对此仍不太满意,紧接着又补了三句:“白面把人吃厌哩,想吃一顿杂面哩,把兀(那)阿达(什么地方)寻见哩!”结果,这首花儿被延长成了极为少见的十句,唱完之后,不但赢得了听众空前的喝彩声,就连对手也不得不表示十分赞赏。这个生动的例子说明,由于歌唱的内容触动了现场听众的内心世界,他们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直接参与了创作,大大丰富了唱词的内容,深化了主题。这种情况虽然并不经常出现,但足以证实听众的参与会产生多么美妙的效果!
朝山进香的善男信女,多数也是花儿的爱好者,甚至就是著名的歌手。他(她)们在殿里敬过神佛、唱过“神花儿”之后,也往往组成一个个小组,参加到对唱的人海中去,或者,挤到对唱的人群里,兴致勃勃地听歌。其中的老年人,对于唱情歌已不再感兴趣,但对本子花儿或表现农家日常生活的花儿却兴趣甚浓。在1985年的花儿会上,有一位叫吴阿婆的老妇,当年己67岁,由于听到青年人们唱情歌,触发了她的思绪,于是便独自一人坐在远离歌唱圈的地方,小声地唱道:“石磨平了重錾哩,骡马老了倒换哩,钢刀老了重磨哩,人老了者咋活哩!”这既是对她自已青春已逝世、晚景凄凉的慨叹,也是不甘心自己的艺术生命被人们忽视和忘却的一种挣扎。她远离人群的歌唱,可说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参与,除了抒发自己孤寂的情怀,也有希望得到同情与理解的因素。
远道而来的观光客人。大都以好奇的心态听歌,他们或因听不懂用方言演唱的歌词而着急,或因偶尔听懂了几句而喜悦。这些客人的音容笑貌,一举一动,甚至穿着打扮,也往往成为“花儿把式”们即兴创作的素材而被顺手拈来,随时编织到歌词中,使双方都大为高兴。
比如1991年,我邀请了一位北京的女记者和两位台湾民间文化专家赴莲花山花儿会采风。四位男歌手就冲着正在拍照的女记者唱道:“斧头要剁白扬呢,北京的尕妹照相呢,今晚给你唱亮呢,明天把你跟上呢,跟上才有希望呢。”这唱词,不仅是触景生情的插曲,也是颇为幽默的玩笑,使在场的听众无不开怀大笑。歌手们要求这位女记者也唱一首花儿,她不会,只好唱了一首流行的通俗歌曲——《黄土高坡》,而歌手们却仍然不饶地唱道:“柴一页,四页柴,北京尕妹好人才,黄土高坡不算数,你把我唱下的花儿补者来!”这位女记者哪能补得上,只好笑着认输。类似这种歌手与听众之间有趣的感情交流,客观上达到了共同娱乐的目的,这在各地花儿会上是屡见不鲜的。
四、赞助者对民间歌手的奖励和权威者对花儿会演唱活动的影响
在以往传统的农业社会里,洮河流域交通不畅,信息闭塞。农民们按节气耕作,靠老天吃饭,文化生活相当贫乏。一年一度的花儿会,就成了他们朝山敬神之后的余兴,是他们唯一的自我娱乐,是对单调农耕生活的重要调剂手段,从来没有靠唱花儿赚钱的念头,也没有丝毫商业演出的意识。正如他们在花儿中所唱的:“杆两根,一根杆,唱个花儿心上宽,不是为的吃和穿。”“你一声来我一声,唱个花儿长精神。”这就是说,农民们在花儿会上所追求的,是满足精神方面的需求,而不是物质利益。
在从前,一些较富裕的地方绅士或商人,出于对花儿的爱好,往往在花儿会上设摊子、管吃喝,用烟、酒、糖、茶、大饼、熟肉来款待歌手们。有的自己掏钱购买许多红绸、红布或红色缎被面,为优秀歌手“挂毛红”表示奖励(最杰出的歌手,一次花儿会可获得十几条“毛红”)。这可说是洮岷一带对花儿歌手们最古老、最传统的赞助和表彰方式。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繁荣民间文化活动,省、地(州)、县三级政府和文化部门,有时也筹措一些资金,在花儿会期间,举办“花儿歌手大奖赛”。参赛的优秀歌手,除了获得奖品(大都是家庭日用品,如毛毯、暖水瓶、被面等)和奖状之外,偶尔也发给他们为数不多的现金补贴。这种赞助方式是一种政府行为,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经常化、普遍化、制度化。
各个花儿会会场附近的农舍和临时搭建的简易帐篷,是四路八乡歌手们最主要的歇脚处,对亲戚朋友一律免费食宿,对不相识的人也只收取少量费用。当地歌手在对唱中有时会这样唱:“鸡毛要扎掸子呢,把你请到我家缓(休息)去呢,要铺个栽绒毯子呢,还要下个细茶碗子呢,给你端个清油卷子呢,还要端成软的呢。”有的则唱道:“手拿镰刀割柳哩,我麦子青棵都有哩,我连旧青棵者煮酒哩,把你能喝几口哩!”“镰刀要割紫草呢,请你吃饱吃好呢,我把肥肉疙瘩高舀呢,把你能吃多少呢!”在食宿方面热情款待远方的亲戚和歌友,是当地农村流传已久的、建立在浓郁乡情和共同爱好基础之上的淳朴风俗,也可以说是一种传统的、群众性的赞助方式吧!
总之,在洮岷花儿流传地区,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性花儿演出形式目前尚未出现。就这一点来说,在当前市场经济大潮汹涌的形势下,它所坚持保存着的古老传统,是很值得重视和研究的。
权威者(这里主要指地方官员)的支持或反对,对于个别人在山林、田野里的歌唱,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但对参加人数很多,有固定地点的花儿会,影响力却很大。在 “文化大革命”中,花儿会被禁达十年之久,的确是“山封了,会占了,歌手撵者不见了,花儿遭了大难了”。
在“四人帮”被打倒之后的1978年,康乐县的个别官员因受极左思潮影响太深,仍然发布禁令,不许人们上山唱花儿,一时群情哗然,纷纷抗议。这件事被媒体曝光后,当地官员迫于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只得撤消禁令,让人们朝山对歌。于是,这一年到莲花山的人数超过了六万人,真可谓盛况空前,热闹异常。
1980年4月20日,身为作家、诗人的甘肃省委书记杨植霖,亲自写信给康乐县文化馆,并创作了几段花儿唱词,表示对花儿会的大力支持,在当地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对后来花儿会的兴旺,产生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权威者因个人好恶或某种政治因素而对传统的民间文艺活动表示支持或反对,在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曾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力。值得庆幸的是,随着改革开放和民主、法制建设的逐步完善,权威个人对民间文艺活动的干涉作用必将被削弱,被限制,直至被彻底否定。而他们对民间文艺活动的支持和热情参与,将会受到广大民众的普遍欢迎。因为,在中国古代史上,上自皇帝,下至县令,在传统的民间节日里与民同乐,被认为是太平盛世的象征,总是受到赞誉,有的还被载入史册,传为佳话。他们数量有限的象征性的资金赞助,远远比不上他们亲自参与在精神上给予老百姓的支持和鼓励。
总之,洮河流域花儿会上的民歌对唱,是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的产物,是农耕文化的一种地域性表现。花儿会是千千万万普通农民展现自己内心世界的绝妙窗口,宣泄自己感情的最佳方式,显露自己才华的重要场所。唱花儿,不但触入了当地农民的日常生活,也融入了他们的生命。人活着,就要唱,“除非把这气咽了,非把这命断了!”
当前的中国,正经受着社会、经济变革的剧烈阵痛,传统的农业文明,也正经受着现代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的巨大冲击。包括花儿会在内的许多传统民间文艺,都面临被包装、被改造、被异化,甚至被淘汰、被消灭的命运。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规律,我们一方面要促进中国人价值观念的进步,并过上现代化的富裕生活;另方面又想让他们的传统文化毫不走样地得到延续,这确实是太难太难了。面对这种两难境遇,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乘花儿会还不至于明显变质的未来数年,抓紧时机,尽快运用科学手段,将它记录、保存下来,并动员和组织各种力量,使这种民间文化能够后继有人。但从长远来看、这种一厢情愿的善意,恐怕不容乐现,只会使人们黯然伤神!因为世界各地民间传统文化的消失和有关史料都证实了这个推断。
注释:
①参见柯杨《花儿溯源》,《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2期。
②参见柯杨《洮岷花儿中的祭祀性歌谣》,《亚细亚民俗研究》第二集,民族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
③这种风俗与当地“驱旱魃”的古俗有关。莲花山一带就曾有过光身女人披头散发,面涂黑灰、手持棍棒,抬着草扎成的“旱魃”爬上山顶,在祭山神的石堆前左转三圈,右转三圈,然后将“旱魃”烧掉,装人布袋,投人洮河,传说这样做了之后老天就会下雨。这种行为,来源于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即所谓“闭阳纵阴,禁火开水”。董仲舒《春秋繁露》中说,古时祈雨,“四时皆以庚子之日,命吏民夫妇皆偶处。凡求雨之大体,丈夫欲藏匿,女子欲和而乐。”因为太阳属阳,雨水属阴;男人属阳,女人属阴。当地过去驱旱魃时,曾唱过“红心柳,两张杈,旱魔怕的娘们家,裤子脱下鞋脱下,不顾羞丑追一呱”的花儿,也有“早魔不怕秃和尚,就怕精身臭婆娘”的俗语流传。(参见云臣《莲花山风情》,载《莲花山》1983年第3期,P.53)
④“本子花儿”是一种以演唱历史故事或道德教化为主要内容的长篇花儿,如《三国演义》、《杨家将》、《二十四孝》、《八洞神仙》、《十二月牡丹》等。
⑤“贺喜花儿”,又叫“搭喜花儿”,主要流传在康乐,临潭一带,是在修庙上梁或在庆贺生了第一个男孩的家庭聚会上所唱的花儿。
⑥在花儿对唱中,如果一方要求另一方用同样的起兴句,押同样的韵,所唱内容还要紧扣所问或所答,往往在末尾加唱一句“你给我原打原的回者来”,对方就必须按要求来唱,并在最前面加一句“原打原的原来了”,以提请对方注意。如果问方不要求“原打原”,答方也可以用“原打原”的方式来唱,以显示自己的机敏和水平。因为提出“原打原”的要求,实际上是故意给对方设置障碍,增加了编词的难度。
最近更新
- 2023-09-11 光明日报等各大媒体纷纷报导“各民族共创中华”论坛暨杨建新先生九十寿诞座谈会胜利召开
- 2023-09-08 “各民族共创中华”论坛暨杨建新先生九十寿诞座谈会会议手册(最新版)
- 2023-09-08 甘肃省优秀研究生“创新之星”项目结项答辩公告(2023年)
- 2023-09-06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 2023-09-06 李占荣
- 2023-09-06 “兰州大学欧盟研究中心”网站链接
- 2023-09-06 第五届“杨建新奖学金“”参评论文获奖名单公示
- 2023-09-03 2023届研究生毕业留影
- 2023-09-02 【会议预告】“各民族共创中华”论坛暨杨建新先生九十寿诞座谈会会议通知(第二轮)
- 2023-09-02 三星堆国家的结构和特征
